
2016年5月,《品图:冀少峰艺术批评文集》正式与读者见面。此书于2014年立项,经过作者两年时间反复推敲、修改而成书,内容分为“立场”、“品图”、“品书”三个部分。采取多学科的立场,运用不同的方法,并把问题置于历史的进程中,从艺术史上下文关系中发现问题,对当代艺术不同门类,不同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本文为“立场”部分的第十三篇文章。
更多内容尽在[雅昌冀少峰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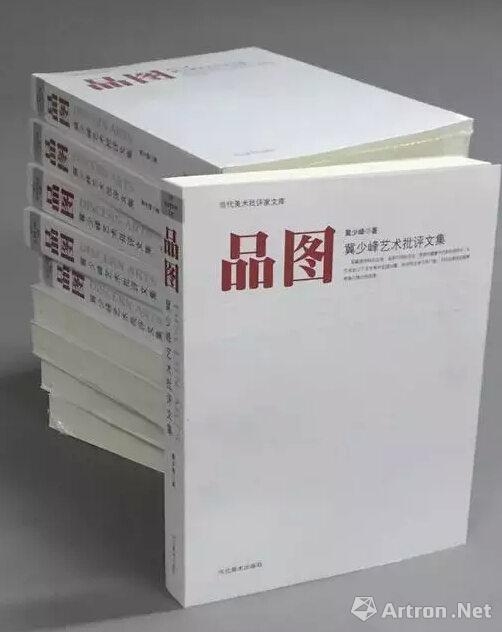
面对纷繁多元的当代艺术状貌,我曾不止一次地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的艺术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
显然,答案是复杂的、多义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无疑是促成中国当代走向多元与多样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还留有那样的记忆:一部文学作品,一幅美术作品,一部电影,均可以引起整个社会的轰动。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这种凭一部作品而扬名的机率就再也难以复制了,它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究其原因,也是人们对于激变的社会和突如其来的陌生时代缺乏思考,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一时代的认知与反思还缺乏精神上和认识上的准备。
应该说,当代艺术在今天之所以还能保持这种激情与活力,也是因为它带有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文化理想和乌托邦精神——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变化,并试图做出某种新的思考和解释。不可否认,转折中的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是以往的社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仅仅靠现成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也难以回答。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从80年代末发展至今的一个进程,其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不仅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包括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激烈的改变。面对巨变的社会和自我,视觉知识分子又能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呢?不难发现,‘短暂的90年代’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的展开的新的戏剧、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析”。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社会的变化呢?
应该看到,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导致了新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领域,尽管我们置身的是现代与传统已经被撕裂的社会现实,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其整体结构、面貌和艺术趣味也的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也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当代艺术以自身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活力与问题意识,逐渐远离了“题材决定论”和“宏大叙事”,而在充满动荡与争议中一路前行,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又能结合当代元素进行有效转换,从而赋予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全球化视野和当代眼光。
参加2010宁波当代艺术邀请展的艺术家以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为主体,在他们身上都不约而同地体现着这么几点共性。
首先,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有着一种别样的精神症候。他们的精神气质似乎很另类,而激进与梦想又赋予了这代人,既不像上一代人(指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参加本次邀请展的方惠民、王晓光即出生于50年代)那样要背负理想的战车去拯救亚非拉人民于水火似的那样沉重,但也没有参加本次邀请展的70后施晓杰、王建,和参加本次邀请展的80后刘梅子们的轻松、幽默与戏谑。历史赋予这代人必定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非常幸运的是他们能够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这也决定了他们理所当然而且必然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历经社会巨变而不惊,他们秉性中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也使他们既能够敏锐地感知时代,但又能和时代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时代的大潮,多元的艺术生态,全球化的侵袭毋庸置疑地把他们推向当代艺术这一视域内。但他们以差异化的表达,个性鲜明的面貌与姿态,以视觉的方式彼此在演绎着他们一代人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诉求。他们从集体主义经验和个人的文化记忆、生存状态出发,去寻求个人自我生存经验的表达,并试图在艺术与人生、生活与梦幻、理想与现实的诸般缠绕和困惑中为人们提供一份清晰的视觉答案。我们清晰地窥视到6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验在他们身上有着清晰的烙印。他们以自我的真诚描述和差异化表达去感知艺术,认识社会,彰显自我对当代艺术与社会人生的敏感体验和把握。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意义追寻和终极关怀这一点上他们又都能保持着一种默契和从容,即他们的艺术是比生活中更真实的存在——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视点转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急速发展及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所引发的消费时代的系列社会问题。他们以独有的表达方式,彰显出都市人的生活情态、生活心态和生活场景。而都市人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在他们那里相互生发,也使他们彼此间的艺术风格又存在着很大差异。